继父的性:“我不想当你爸了,叫妈妈吧!”
|
仙剑98柔情版下载 我十岁之前,父亲的梦想是当歌星,他不仅会唱流行歌曲还会唱戏,家里的三洋双卡收录机从早唱到晚,唯一安静时光,便是收录机坏了,父亲会忙不迭扛着机器“噔噔瞪”下楼找人修。 父亲每天都会刮胡子,对着镜子梳理大背头,左手戴手表,右手戴一串黑色手串,一身平整服帖的白衣裤,他说白色象征纯洁,给人干净清爽的感觉。 父亲爱烧菜,他烧的青螺和龙虾总是让我垂涎三尺,家里来客人时,他对酒当歌,把啤酒瓶当话筒,歪头闭眼,用粤语演绎那首当时风靡的光辉岁月。 我十岁生日那天,父亲起早去郊区河塘摸了一斤多青螺,在菜场买了一把去腥提鲜的紫苏,做了满满一桌菜,母亲却连筷子都没动,两只眼睛凄惨惨,像是将要送往屠宰场的老牛,充满绝望。 第二天,父母就领了离婚证,父亲把唯一的房子给了陪伴他十一年的女人。 父亲一直追逐他的歌星梦,家里开销主要由母亲和爷爷承担,爷爷退休工资都补贴了家用,可是年初爷爷去世了,母亲不堪重负,她要的是一个可以承担家庭责任的丈夫,而不是一个在家又蹦又唱的男人。 我以为我会跟母亲生活,但事实并没有,母亲用灰色蛇皮袋装好我跟父亲的行李,缓缓打开锈迹斑斑的防盗门,用眼神示意我跟父亲,你俩可以离开了。 我恨母亲,更恨父亲,怨恨的种子在我心里从一个点渐渐扩散成一支军队,一部分一部分将我攻陷。 我在简陋出租屋里哭得天昏地暗:“我没家了,我没家了,妈妈竟然不要我了,她有房子还把我赶走!” 父亲坐在我身旁,脸上蒙着一层灰暗,肩膀塌了下去:“女儿相信爸爸,爸爸会给你一个家的,不会让你居无定所。” 我抬起头,擦干泪,用双拳捶打父亲胸口:“别人家爸爸都好好上班,就你整天在家咿咿呀呀唱歌,又不挣钱!” 我越说越气,站起身使出浑身力气,摔了父亲的三洋收录机,父亲面孔痉挛,喉结耸动,蹲下身,双手捂住脸。 从那之后,父亲的梦想就是给我一个安身的小窝。 父亲开始找工作,那时智能手机还没普及,父亲每天早早起床,到门外吊一会嗓子,然后买一份报纸,伏在桌上挨个打电话问,他没手艺,没文化,只有力气,最后在一家工地扛大石头。 父亲第一天回家时,腰是弓着的,右手支在右腿上,眼睛红肿,不是哭的,是被汗水腌的,白色衣裤变得灰扑扑,我赶紧扶他躺下,父亲大喊:“女儿,不能躺,得趴着,背烂了。” 我心一揪,父亲脱了短袖我才看到背脊上那触目惊心的血痕,肉皮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,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。 “闺女,没事,老师傅说了,磨出茧就好了,我没正儿八经上过班,不知道赚钱这么难。” 那一晚我是在父亲低沉的呻吟声中睡着的。 父亲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五年,依旧一身白衣裤,头发纹丝不乱,脸上清爽爽,只是眼角有了细细纹路,难得空闲就在家打开三洋收录机,小声跟着哼几句。 我读初三那年,父亲失业了,长期重体力劳动使他得了腰肌劳损,医生说他不能再干重活,父亲一脸凝重,蹲在角落可怜巴巴看着报纸,寻找他能胜任的工作,两张嘴要吃,房租要交,还有我的学费。 那段时间,父亲找工作频频受挫,嘴上起了一溜泡,我侧躺床上凝视房间发霉墙角,父亲说会给我买房子,如今别说买房子了,一日三餐能吃饱都难!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,父亲很快找到了讨生活的方法,他厨艺够不上厨师水准,但做青螺和龙虾味道却是绝对,他买了一个不锈钢桶,白天在家做好青螺和龙虾,晚上骑自行车带到夜市大排档去推销。 父亲晚上6点出门,天蒙蒙亮回家,或许是味道确实好,桶每天都见底,家里饭桌上有了荤菜,父亲给我订了牛奶,带我去书店给我买参考书和名著,去超市时他会羞答答往购物车放我用的卫生巾。 有时我也会跟他聊心事,挑眉故意问他:“爸,妈为什么不要我?” 父亲放下手里洗刷的青螺,抬起头,欲言又止,最后小声说:“女儿,等你长大后,爸爸才能告诉你。” 我垂首不语,捏起一颗青螺,细细洗刷。 父亲赚的钱除去日常开销外,会小心翼翼放在一个白色信封里,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五个大字:买房子的钱。 中考结束,我跟同学去大排档开荤,我竟然看到了父亲,父亲在我前面一桌卖力推销他的青螺和龙虾,说得舌敝唇焦,其中一个顾客说:“被你说得烦死了,买一盒吧,听说买你东西,你会唱一首歌。” 父亲点头如捣蒜:“这一片,谁不知道我罗哥天生好嗓子,我的歌声可以让人忘记烦恼。” 父亲头歪在一边,翘出兰花指,眯着眼,水蛇似的扭动身躯,“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可拥有,只相信是靠双手,每一滴汗水换一个成就。” 父亲已没了当年唱光辉岁月时的激昂豪迈,一桌人根本没人听他唱歌,只是被他那娘娘腔的声线和滑稽神态逗弄得前俯后仰! “听说你很能喝!你十秒内喝完这瓶啤酒,我们就再买你一盒龙虾。” 父亲捂嘴一笑,立马拿起桌上一瓶啤酒,深吸口气,仰头咕噜咕噜喝,一桌人表情兴奋,双手拍掌,集体喊着:“十,九,八,七,六,五,四,三,二,一。” 数到一时,父亲刚好喝完,大概是喝得太急,刚放下瓶,立刻蹲下来吐了,没人俯身多看他一眼,他吐完擦干嘴站起来,众人又起哄:“吐了不算,再喝!” 父亲咧嘴一笑,接过酒瓶,仰头继续喝。 当他歪歪倒倒走到我们桌时,我垂着头,脸上火辣辣,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,父亲应该看到我了,他只停留了五秒左右就走了,但一个眼尖的同学还是认出了他:“丽丽,那个娘娘腔不是你爸嘛?他怎么在这卖唱啊?” 那一刻我的自尊心被碾成了粉,我哭着离开了座位,追上父亲,梗着脖子质问他:“你为了赚钱非要把自己弄成一个娘娘腔吗?你哪里是推销龙虾和青螺,根本就是陪酒卖唱!” 父亲鼻翼翕动,杵在原地,不停仰头,不让泪水流下来:“女儿,爸爸老了,高音已经上不去了,只能唱一些平缓的曲调,词曲是我自己编的,我融入了戏曲的元素,并不是你说的娘娘腔。” 我根本接受不了父亲那套说辞,趁白天父亲睡觉间隙,偷偷把他装菜的不锈钢桶扔了,逼他出去找工作,父亲只是深深叹气,第二天买了新桶,骑着自行车继续开工。 那天早上,我起床后,父亲还没回家,我隐隐有种不好预感,穿上衣服出去寻找父亲,走了十分钟,我看到马路边围了一群人,我钻进人群,躺在地上的竟是父亲! “爸爸,你怎么了,爸爸,你怎么了,你说话啊!” 父亲费力抬起眼皮,在我耳边嗫嚅道:“不去医院,我就是想睡一会,累。” 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每天收工时除了满身疲惫外,还有满胃酒精,他骑车时头是晕的,身子是摇晃的,实在太累,他会停下车,蹲在路边靠墙睡会。 那几天我在家发脾气,他白天也休息不好,收工骑车回家时,眼皮实在抬不起来,龙头没操控好,摔倒在路边。 父亲醒来时,整张脸都浮肿起来:“女儿,好好读书,没文化,没手艺,赚钱很幸苦的。” 我泪如雨下:“爸,对不起,我不该瞧不起你。” 高中时,有一天父亲兴匆匆跑到我学校对我说:“女儿,爸找到一份好工作,工资可高了,你不是不喜欢爸爸在大排档抛头露面,以后不会了。” 父亲新的工地方是一个专门做夜宵的馆子,父亲说很大,分上下两层,馆子的老板慧眼识珠,把父亲挖到他馆子唱歌。 父亲跟我说,他晚上6点上班,凌晨2点下班,只负责唱歌。 父亲的收入确实多了起来,家里的白色信封一天比一天鼓,装满一个又一个,父亲喝醉时就会蹲在角落一遍遍数钱,边数边笑:“女儿,房价又涨了,不过不怕,爸爸会卖命工作,肯定会给你买套房,给你房间贴满粉红色的大脸猫。” 我擦擦父亲额头汗珠:“那叫hellokiity,爸,你供我读书已经不容易了,我又不用娶媳妇,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。” 父亲头一昂:“爸爸答应过给你一个家,以后在婆家受气有个自个儿小窝多好。” 我捂嘴一笑,不知何时,父亲脸上有了一股迟暮之气,手也开始抖了起来,那是酒精性震颤。 父亲一直不愿告诉我他工作的地址,他说我去的话,会影响他发挥,唱不准音会被老板扣工资。 后来我去外地读了大学,父亲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给我打电话,絮絮叨叨说很多事,他大概真的老了,一件事能反复说三四遍,我笑他真是越来越健忘了。 大学期间,我抓住一切机会勤工俭学,我是受过贫穷折磨的人,对金钱有超出常人的渴望。我只有过年才会回家,父亲搬了家,屋子宽敞向阳,不再像以前,阴暗逼仄,墙角发霉。 毕业后我选择回老家陪在父亲身边,父亲翘首站在车站,见我扛着大包小包回来,激动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,又哭又笑,背脊佝偻,额头皱纹深得已经能夹死苍蝇了。 “闺女,爸爸终于攒够首付的钱啦,城东有个楼盘下月开盘。” 父亲终于要兑现他曾经许给我的诺言了,我也满心期盼家的模样,可惜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。 那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医院电话,父亲眼睛被炸伤,必须摘除眼球,我放下电话泪如山洪,奔向医院。 医生告诉我,父亲的右眼是被鞭炮炸伤的,已经保不住了,必须摘除,医生说完斜睨一眼旁边杵着的男人。 男人脸窄身薄,是父亲老板,瞳眸里满是惊慌:“没....我跟你爸没签合同,我顶多赔偿手术费。” 我眼泪鼻涕混在一起,抓起男人衣领,大声吼:“你对我爸做了什么?他不是在你店里唱歌吗?怎么会炸掉眼睛?” 男人一脸诧异:“你爸早就不唱了,他没告诉你他现在做什么吗?” 父亲做完手术后,眼睛围着厚厚白纱布,整个人变得沉默了,坐在床上不发一语,像一尊劣质雕像,我知道父亲需要时间接受这一切。 我独自来到父亲工作的馆子,要了一瓶啤酒,一楼的舞台已经开始了表演,表演者赤裸的上身缠满红色小鞭炮,整个人被玻璃罩罩住,玻璃罩是怕鞭炮炸到客人,随着鞭炮连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,台下客人情绪被充份调动,挥舞双手,瞳孔放大,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。 鞭炮炸完后,玻璃罩内烟雾缭绕,我看不到表演者的表情,他应该很疼,可这就是他工作,我又想起父亲那句话,女儿我没手艺,没文化,赚钱不容易的。 我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他上班的地点。 父亲后来告诉我:“我一开始确实是去唱歌的,但没多少人听我唱歌,老板也觉得有我没我一个样,想开除我,我急啊,房子钱还没攒够,正好当时表演炸炮仗的那个人不做了,这种危险的活工资高,但没人敢做,我就做了,我要给你买房子,我答应过你的。” 我垂着头,摩搓着双手,父亲被鞭炮炸时心里该是多么害怕,我轻轻捋起父亲上衣,肚子上,背上,肩膀上,都是密密麻麻的灰疤,触目惊心,我鼻头一酸,眼泪止不住流。 父亲摘除眼球后,买房的钱花了一部分用来给他装了义眼,买房就耽搁了。 父亲每天坐在出租屋里无所事事,非常焦虑,他说他嗓子还能唱,想出去找事做,可是哪里有人要他呢? 我苦口婆心安慰父亲:“爸爸,我年底拿了年终奖就能凑齐首付钱了,你就在家好好呆着。” 父亲蹙眉撇嘴,凑近我耳朵,小声说:“房子还没给你买呢,我心悬着呢。” 父亲真是闲不住,戴了墨镜拖着音箱,去夜市卖唱了,客人点什么他唱什么,一首歌十块钱,他就这样一天天攒钱,每晚回家,嘴里哼着小曲,把皱巴巴的钱往信封里塞。 父亲回家时间越来越晚,我去夜市找他,有时还会跟他合唱一曲,父亲音线低沉,多了几分岁月沧桑,每次跟我一起唱,父亲都会告诉听客,我是他女儿,是他心头肉,他这辈子虽没当上歌星,但把我抚养成人,此生无悔。 渐渐的父亲开始忘词,出门开始丢三落四,有次我下班回家,父亲没有去夜市唱歌,而是怔怔看着我,歪着头问我:“你是谁?” 那一刻我的世界天崩地裂,我知道父亲得了什么病,可是我明明已经赚够了房子首付的钱,父亲啊,你不是一直等着这一天吗? 好在父亲的病还是早期,偶尔还是能认识我,我请了搬家公司,用最快的速度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,把朝南的屋子给了父亲,把他心爱的三洋录放机擦干净,轻轻放在他床头。 父亲常常凝视那台三洋录放机发呆,用手轻轻抚摸,喉咙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,有时用笔在白纸上画房子,拿给我看,咿咿呀呀说:“买……房子。” 我凑到父亲耳边,轻声细语说:“爸,这房子就是你攒钱买的啊。” 父亲一愣,站起身环视屋子,走到墙边用手轻轻抚摸墙壁,喃喃道:“我买的?” 我紧紧抱住父亲在他耳边说:“爸爸,你答应我的已经做到了。” 父亲歪着头笑,口水滴到衣领上,我用手轻轻拭去,如果父亲清醒绝对受不了自己如今邋遢模样。 “爸,你还没有告诉我,为什么当初我妈不要我。” 父亲对我吐吐舌头,转过身步履蹒跚进了房间,我不知他是不是真的没听懂。 其实我知道问题答案,父母刚离婚时,我非常想念母亲,偷偷跑回去找过母亲,当时我站在门口,听到母亲说。 “老孙没本事赚钱,老头子又走了,家里穷得叮当响,可老孙就是不愿把丽丽送走,他说他再穷也不会像丽丽亲生父母一样,把丽丽仍在医院门口,他想做活菩萨,我可不想跟着他穷一辈子。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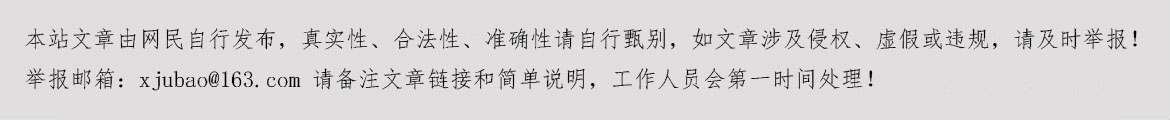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
